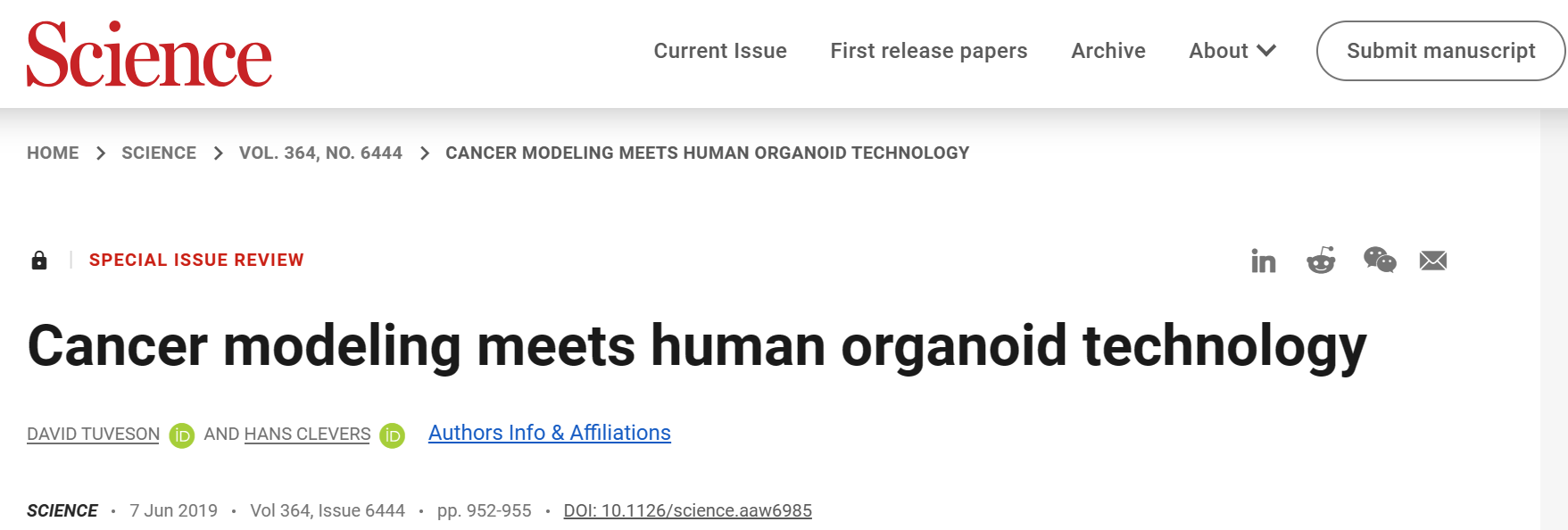2009年,来自荷兰的Hans Clevers团队在体外三维(3D)器官培养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地在体外培养出有自我更新能力、保持肠道腺窝绒毛状结构的小鼠肠道类器官(gut organoids)【1】。自此,类器官技术(organoids technology)在人类科学研究发展史中拉开了帷幕。

类器官(organoids),顾名思义,类似器官的模型,是一类由干细胞,包括多能干细胞(pluipotent stem cell, PSC)和成体干细胞(adult stem cell, ASC),在体外培养时形成的能够进行自我组装的微观三维结构。因其与对应的器官拥有类似的空间组织、保持一些关键特性并能够重现部分生理功能,而被认为是检测人类生物学和疾病方面的新模型。相较于细胞系(cell lines)、基因工程鼠(genetically engineered mouse models, GEMMs)和人源化异种移植鼠(patient-derived xenografts, PDX)这些传统的研究模型,类器官模型(鼠源类器官mouse-derived organoids,MDO和人源类器官patient-derived organoids,PDO)不但能够取自正常组织和组织癌变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肿瘤组织,而且其培养体系简单易操作,时间和金钱成本较低,且具有较高效率,因而得到广大研究人员的亲赖,被
Nature Methods评为2017年生命科学领域年度技术。

2019年6月7日,来自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的David Tuveson和荷兰Hubrecht 研究所的Hans Clevers在Science共同撰文Cancer modeling meets human orgaonid technology,总结了如何将类器官技术应用于癌症领域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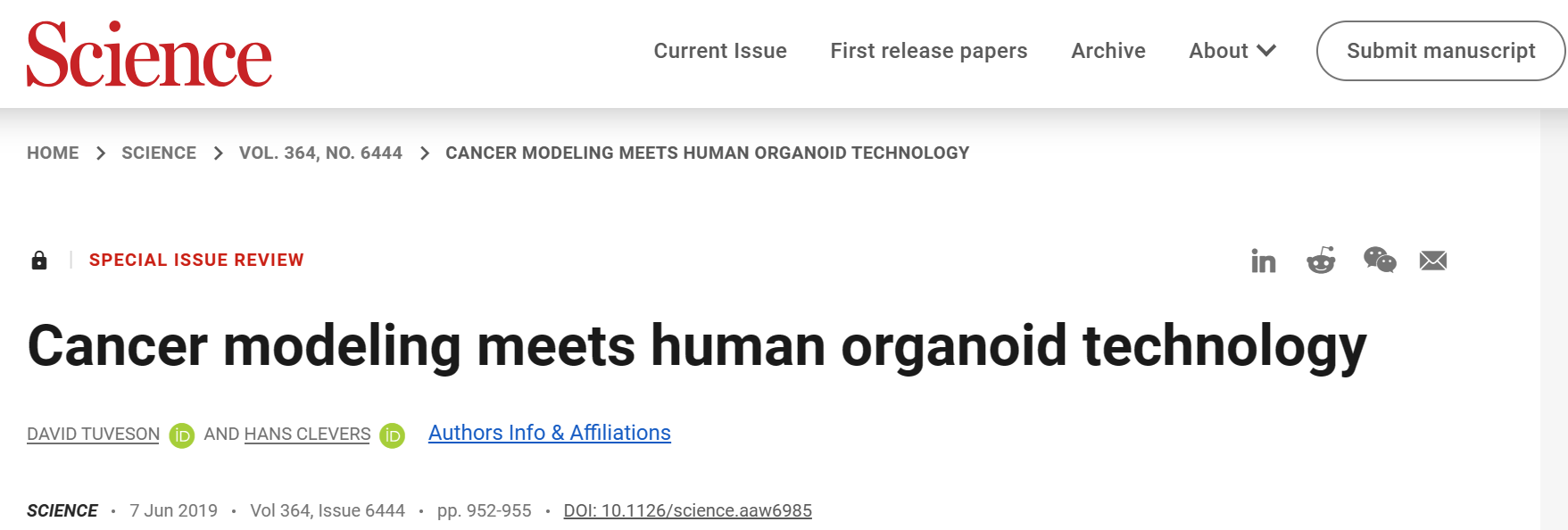
一、创建肿瘤类器官生物样本库(biobanks)
目前,癌症联盟组织如国际癌症基因组联盟(International Cancer Genome Consortium,ICGC)、癌症基因组图谱计划(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所使用的大部分样本都取自于原发肿瘤(primary tumors)。相比之下,PDO可以取自肿瘤发展过程中的任何阶段,而且只需要一小部分肿瘤组织即可在体外进行培养和扩增。研究人员已经在肝癌【2】、胰腺癌 【3】 和结肠癌肝转移【4】组织中,通过穿刺获得活检,成功的在体外进行类器官培养。Gao et al甚至能够将前列腺癌患者的循环肿瘤细胞在体外培养成类器官【5】。也有研究人员从尿路(urine)【6】和支气管肺泡(bronchial lavage)【7】 的正常细胞中成功培养类器官,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培养方法能否适用于这些组织来源的肿瘤类器官培养。
体外培养的PDOs能够很好的反应大部分肿瘤组织(bulk tumor)所具有的特性【4】。举例来说,从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组织和癌旁正常组织中提取并培养的PDOs,通过分子机制和功能学分析可以发现,相比于正常的细胞,CRCs细胞具有大量且多样性的突变【8】。虽然,每个肿瘤内DNA甲基化多样性和转录组状态是稳定的,但是,即使是在同一个肿瘤当中,抗癌药物反应却是有所不同的,这说明表观遗传改变(epigenetic changes)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细胞的基因表达,形成肿瘤异质,呈现不同的药物反应。这也是目前类器官技术面临的一大挑战,即如何能够更好的追踪和分析瘤内异质性。除此之外,另一大挑战是在长期培养过程中,如何保证类器官不发生克隆漂变(clonal drift),尽管有研究表示这个发生的几率很小【9】。
因此,针对各种不同突变细胞(或谱系)和不同器官组织所衍生出的类器官,为了能够优化其长期培养条件,同时更好通过类器官认识和研究肿瘤发生发展过程,建立类器官生物样本库是很有必要的。目前,荷兰非盈利类器官技术组织HUB(www.hub4organoids.eu)已经建立了类器官生物库,与ATCC(American Type Culture Collection)类似,具有超过800种已知遗传信息等特性的不同类器官,供科研院校和公司企业选择使用。同时,人类癌症模型倡议组织(The Human Cancer Models Initiative, HCMI)也在不断建立不同的肿瘤培养模型,并将其发展成为共享资源。
类器官技术能够体外模拟组织癌变过程
在研究组织癌变过程中,肿瘤类器官除了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肿瘤组织中获取,也可以通过对正常的类器官进行基因编辑获得,后者能够单纯地研究某个基因或某些基因组合的功能。
以CRC为例,根据腺瘤癌变次序论(adenoma-carcinoma sequence),CRC的发生发展过程是一系列基因按照特定顺序接连发生突变的结果。J. Drost et al通过使用CRISPR/Cas9技术,依次在肠类器官内突变APC, P53/TP53, KRAS 和 SMAD4后发现,突变后的肠类器官可以不依赖于任何外源细胞因子而进行生长和繁殖。当把同时具有四种突变的类器官重新移植到小鼠时发现,这些类器官诱导发生的CRC具有侵袭性(invasive CRC)【10】。A. Fumagalli et al 进一步证实,有且只有四种突变同时发生时,肿瘤才能够发生转移【11】。类似的,研究人员通过在正常巴雷特食管类器官突变APC使得细胞发生癌变 【12】;在正常大肠类器官内同时突变Braf、Tgfbr2、Rnf43/Znrf3和P16/Ink4A而获得具有锯齿状特性的腺癌 (serrated adenocarcinoma ) 【13】;在正常胰腺类器官内依次突变KRAS, CDKN2A, TP53, and/or SMAD4而生成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s)【14】。此外,编辑过的类器官也可以进行亚克隆分选,进而更好的研究基因功能。比如敲除关键的DNA修复基因并对突变的类器官进行亚克隆后培养发现,有新的特定突变特征(mutational signature)的产生【15】。得益于近年来干细胞基因敲入技术,类器官变得可视化。Sato T et al通过对干细胞标记物LGR5进行谱系示踪后发现,肿瘤发生过程中,LGR5+细胞具有肿瘤干细胞特性,能够进行自我更新和分化能力 【16】。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将LGR5+肿瘤细胞敲除后,出现了短暂的肿瘤退化,之后,由KRT20标记的分化肿瘤细胞能够重新转变为LGR5+自我更新的肿瘤干细胞,进而继续促进肿瘤的生长,这表明了CRC的肿瘤生长依赖于LGR5+的肿瘤干细胞,同时,已经分化的肿瘤细胞也可以去分化成干细胞以补充肿瘤干细胞池内的细胞缺失【16】。目前,基于ASC的类器官技术无法进行正常的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组织进行培养,但是,PSC衍生的类器官却可以很好的模拟脑瘤的发生发展过程【17】。
二、类器官共培养技术助力表征肿瘤微环境和免疫治疗
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是肿瘤细胞赖以生存的地方,无时无刻的影响着肿瘤细胞的发生发展,然而,目前的研究技术手段还无法对微环境进行表征。尽管肿瘤类器官培养体系并没有包含完整的TME,然而,一些研究发现,将TME内特定类型细胞与肿瘤类器官进行共培养,可以在一些方面对TME进行表征。将胰腺星型细胞与胰腺癌PDOs进行共培养后发现,这些星型间质细胞开始向胰腺肿瘤特有的纤维化特性间质细胞转变,有一部分甚至已经分化为肿瘤相关性成纤维细胞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CAF) ,他们通过分泌IL-6促进类器官繁殖【18】。通过胰腺癌PDOs和CAF共培养发现,肿瘤PDOs能够诱导生成不同的CAF亚型,为肿瘤内调控CAF组成提供依据【19】。
除了间质细胞之外,微环境中另一种重要组成细胞是免疫细胞。目前与免疫细胞共培养技术的探索还处于相对早期的阶段。来自美国的Kuo团队从2009年就一直尝试使用气液交互(air-liquid interface,ALI)类器官培养技术还原原代肿瘤组织和微环境。2018年,他们通过使用该方法将PDOs和免疫细胞或成纤维细胞进行一体化共培养,在长达数周的时间里,病人T细胞克隆的多样性仍然被很好的维持下来; 他们也顺利地将这个技术应用于评估免疫检查点治疗效果【21】。除此之外,将具有高突变负荷或烟草相关非小细胞肺癌的PDOs和对应病人的外周血进行共培养, 这些PDOs能够很好地向T细胞呈递抗原,从而使CD8+ T细胞激活和增值【21】。原则上来讲,这种方法可以在体外获得大量效应T细胞,然后对病人进行过继T细胞治疗。
三、类器官技术正在成为个体化治疗的工具
运用类器官技术进行个体化治疗是指,通过体外对类器官进行药物筛选和基因型分析,制定适合这个个体的治疗药物和方法。截至到目前,不同肿瘤PDOs对传统和正在研发的药物所产生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对目前有限的资源研究发现,大部分PDOs所展现的治疗反应和相对应的病人刚开始对治疗的反应是一致的【22-26】。PDOs也可以用于针对被动或获得性耐受开发新的药物【23】。更重要的是,PDOs对具有细胞毒性的药物敏感性较强,因而可以更好的预测病人使用后的临床反应【24-26】。接下来,研究人员对大量个体PDOs的药物反应数据进行整合分析,找出共同特征,进而对一类相似病人进行生物标记物开发研究【24】。
人们同时希望能够将类器官技术应用成为类似“细菌检测”一样简单的“个体癌症检测”,美国Blue Ribbon Panel for the Cancer Moonshot也将这个想法提上了议程。目前的临床实验研究可以将从有限个体中得出的结果(也即以经验为依据的PDOs反应)运用于大量同类型的病人,同时,新开发的化疗药物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检测。如果在大量样本中,PDOs的经验检测(empiric test)效果很好,那么,就可以扩大设计合适的临床实验(clinical trial)。
四、机遇与挑战并存
目前的类器官技术也面临着大量挑战,从类器官本身而言,不同器官肿瘤模型形态不易区分、不具有代表性;培养周期较长;培养价格还不算亲民;高通量药物筛选和免疫治疗筛选方法还不够完善等等;从微环境而言,除了和免疫细胞或成纤维细胞进行共培养,如何能够将血管和神经细胞加入培养体系中进行多维培养等等。然而,作者们始终相信,类器官技术会极大的促进基础研究领域和临床治疗方面的研究,成为他们的好帮手。
致敬并纪念为现代类器官做出卓越贡献的Yoshiki Sasai
Yoshiki Sasai (1962—2014-8-5)发育生物学家、干细胞、类器官科学家。生物学界对他的评价:“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辛苦努力的基础上。” “是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 “Sasai的工作给人以灵感。”
参考文献
[1] T. Sato et al., Nature 459, 262–265 (2:009).
[2] S. Nuciforo et al., Cell Rep. 24, 1363–1376 (2018).
[3] H. Tiriac et al., Gastrointest. Endosc. 87, 1474–1480 (2018).
[4] F. Weeber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2, 13308–13311 (2015).
[5] D. Gao et al., Cell 159, 176–187 (2014).
[6] F. Schutgens et al., Nat. Biotechnol. 37, 303–313 (2019).
[7] N. Sachs et al., EMBO J. 38, e100300 (2019).
[8] S. F. Roerink et al., Nature 556, 457–462 (2018).
[9] M. Fujii et al., Cell Stem Cell 18, 827–838 (2016).
[10] J. Drost et al., Nature 521, 43–47 (2015).
[11] A. Fumagalli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4, E2357–E2364 (2017).
[12] X. Liu et al., Cancer Lett. 436, 109–118 (2018).
[13] T. R. M. Lannagan et al., Gut 68, 684–692 (2019).
[14] T. Seino et al., Cell Stem Cell 22, 454–467.e6 (2018).
[15] J. Drost et al., Science 358, 234–238 (2017).
[16] M. Shimokawa et al., Nature 545, 187–192 (2017).
[17] S. Bian et al., Nat. Methods 15, 631–639 (2018).
[18] D. Öhlund et al., J. Exp. Med. 214, 579–596 (2017).
[19] G. Biffi et al., Cancer Discov. 9, 282–301 (2019).
[20] J. T. Neal et al., Cell 175, 1972–1988.e16 (2018).
[21] K. K. Dijkstra et al., Cell 174, 1586–1598.e12 (2018).
[22] S. H. Lee et al., Cell 173, 515–528.e17 (2018).
[23] S. J. Hill et al., Cancer Discov. 8, 1404–1421 (2018).
[24] H. Tiriac et al., Cancer Discov. 8, 1112–1129 (2018).
[25] G. Vlachogiannis et al., Science 359, 920–926 (2018).
[26] C. Pauli et al., Cancer Discov. 7, 462–477 (2017).